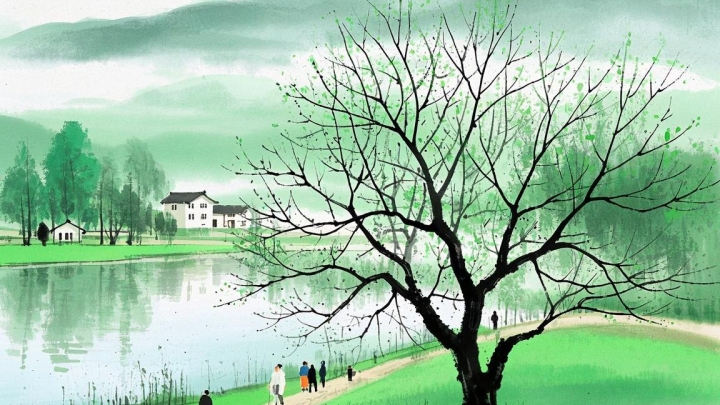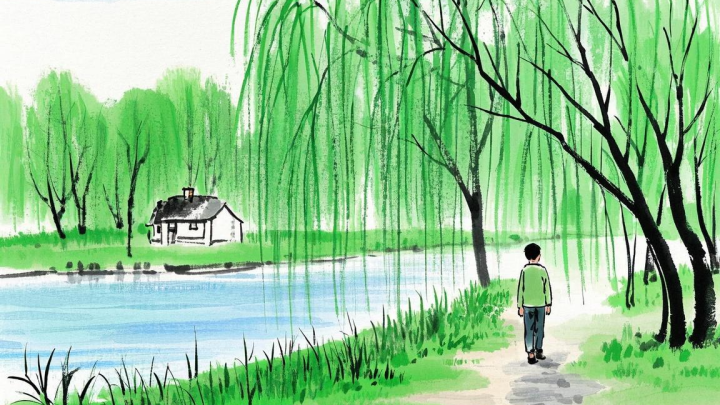
那是厂子里搞“技术大比武”的时节。
车间里的车床转得嗡嗡响,机油味混着铁屑的腥气,灌满了整个厂房。
我是三车间的铣工,进厂五年,手上磨出的茧子能刮擦砂纸。
媳妇在纺织厂三班倒,常年带着一股棉纱的味道,说话嗓门大,夜里总嫌我身上的机油味熏着她。
那天下午,我正猫着腰调试铣床参数,额头上的汗滴在操作台面上,砸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。
“哎,师傅,这台机床的进给量怎么调?”
声音清亮,像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,带着点脆生生的甜。
我直起腰,转头看见个穿蓝布工装的姑娘。
她扎着麻花辫,发尾系着根白纱巾,袖口挽得老高,露出半截手腕,皮肤是那种常年不见太阳的细白。
“你是哪个车间的?”我拿袖口擦了把汗,机床操作台上的油污蹭到了脸颊。
“劳资科的,新调来的统计员,”她指了指机床面板,“王科长让我来跟岗学习,说铣工最练眼力。”
她叫林晚,名字里带个“晚”字,说话却像早上的雀儿,叽叽喳喳停不住。
“这台铣床得先校准坐标系,”我拿起扳手,拧了拧固定螺栓,“进给量要跟着转速调,太快了刀头容易崩。”
她蹲在我旁边,膝盖上放着个牛皮笔记本,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写。白纱巾垂在肩后,随着她低头的动作轻轻晃。
“师傅你姓陈?”她忽然抬头,睫毛很长,眨眼睛的时候像蝴蝶扑棱翅膀,“我看你工牌上写着陈建国。”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,心里有点发慌,赶紧把注意力拽回机床上。
车间里的老油条们开始吹口哨,李师傅扯着嗓子喊:“建国,带徒弟呢?这姑娘水灵!”
我脸一热,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地上。林晚却像没听见,把笔记本往我面前一递:“师傅,你看我记的对不对?”
纸上的字迹娟秀,跟她咋咋呼呼的样子不太像。她还在“进给量”三个字旁边画了个小齿轮。
那天傍晚下班,我收拾工具包,发现帆布兜子里多了个油纸包。
打开一看,是两个白面馒头,中间夹着酱牛肉,肉汁渗进馒头里,染出一圈深棕色。
旁边还有张字条,是那种办公用的便签纸,写着:“看你中午啃干馒头,这个顶饿。——林晚”
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,像被机床的卡盘夹住了似的,又麻又涨。
我结婚三年,媳妇从没给我带过午饭。她总说纺织厂活儿累,回家只想躺着。
第二天上班,我把洗干净的油纸包还给林晚,里面塞了两个我妈腌的咸鸡蛋。
“谢谢你的馒头,”我把纸包往她手里一塞,“我妈腌的蛋,不咸。”
她接过去,笑出两个梨涡:“陈师傅,你这人真有意思,送吃的还带还礼的。”
从那以后,林晚常来三车间。
有时是送报表,有时是“请教”机床知识,更多时候是端着个搪瓷缸,站在我机床边看我干活。
她会把白纱巾摘下来,系在操作台的手柄上,说这样“看着利落”。
有次我铣一个弧形零件,刀头突然崩了,铁屑四处飞溅。
我下意识把她往身后一推,自己胳膊上划了道口子,渗出血来。
“呀!”她惊叫一声,从口袋里掏出块手帕,“快擦擦,是不是很疼?”
手帕是细棉布的,印着淡蓝色的小碎花,带着股肥皂的清香味。
我没接,只把胳膊往袖子里缩:“小伤,没事。”
她却不管,抓住我的手腕就往医务室拉。她的手心很暖,指尖有点凉。
医务室的王大夫边涂红药水边笑:“建国,这姑娘对你挺上心啊。”
我没说话,林晚却接茬:“王大夫,他是为了护我才划伤的,我得负责。”
那天之后,车间里的闲话更多了。
有人说林晚看上我了,有人说我媳妇知道了要闹翻天。
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。我知道自己配不上林晚,她是高中生,长得又秀气,而我只是个满身机油的铣工,家里还有个爱吵架的媳妇。
直到那天晚上,我回家撞见媳妇跟邻居张姐在院里说话。
“……他车间来了个小姑娘,天天往他跟前凑,”媳妇的声音尖得像锥子,“穿得溜光水滑,一看就不是正经人!”
我推自行车的手顿了一下,车链条发出“咔哒”一声响。
媳妇回头看见我,立刻叉着腰走过来:“陈建国,你行啊!在车间勾三搭四,当我不存在?”
“你胡说什么!”我把自行车往墙上一靠,声音也拔高了,“林晚是来学习的,我们什么都没有!”
“什么都没有?”媳妇冷笑,“那人家为啥给你带吃的?为啥拉你去医务室?你当我眼瞎?”
我们在院子里吵了起来,邻居们都扒着窗户看。
媳妇越说越难听,什么“没良心”“陈世美”全骂出来了。
我气得浑身发抖,抓起放在门口的工具包,扭头就走。
鬼使神差地,我走到了三车间的后窗下。
车间里还亮着灯,林晚坐在我的机床边,正对着图纸发呆,白纱巾搭在椅背上。
我敲了敲窗户,她吓了一跳,看清是我,赶紧跑出来开门。
“陈师傅,你怎么来了?”她看见我手里的工具包,愣住了,“你……跟家里吵架了?”
我没说话,只是靠在门框上,觉得浑身没劲。
车间里很安静,只有远处风机的嗡嗡声。林晚给我倒了杯热水,杯子是她自己的,印着朵粉色的月季花。
“我听见院里吵架了,”她把杯子塞到我手里,“阿姨……你媳妇,是不是误会了?”
“是我没处理好,”我喝了口热水,喉咙里火烧火燎的,“她……就是那样的人。”
林晚没再问,只是坐在我旁边,陪着我发呆。
白纱巾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,像一团云。
“陈师傅,”过了很久,她才轻声说,“其实你人很好,就是太闷了。”
我转头看她,她的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,像落了星星。
“你不该总被家里的事压着,”她把白纱巾从椅背上拿下来,在手里绕着,“你看你铣零件的时候多专注,跟换了个人似的。”
我的心又开始跳,比机床最高转速时还快。
我想伸手摸摸那根白纱巾,想告诉她我心里的憋闷,可我不能。
“林晚,”我把杯子放在地上,声音有点哑,“你以后别来三车间了,省得别人说闲话。”
她愣住了,绕着纱巾的手指停住了。
“是不是因为……你媳妇?”她的声音有点低。
“是,也不是,”我站起身,“我……我配不上你这样的姑娘。”
说完,我没敢看她的表情,抓起工具包就往外走。
身后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,显得格外狼狈。
从那以后,林晚果然没来三车间了。
我心里空落落的,干活也没了劲头。媳妇倒是消停了些,但我们之间更冷淡了,像隔着一堵墙。
厂里要选派一批工人去外地进修,我报了名。
离开那天,我去劳资科交材料,正好碰到林晚。
她瘦了些,白纱巾换成了素净的蓝头绳。
“陈师傅,听说你要去进修了?”她接过我的材料,语气很平淡,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“嗯,”我点点头,“去半年。”
“挺好的,”她低头翻着材料,“好好学习,回来能评技师。”
我想说点什么,比如“对不起”,比如“谢谢你的馒头”,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“那我先走了。”我转身要走。
“陈师傅,”她忽然叫住我,“这个……给你。”
她从抽屉里拿出个牛皮纸袋,塞到我手里。
“路上吃,”她笑了笑,还是有两个梨涡,“别总啃干馒头。”
我捏着纸袋,里面硬硬的,像是饼干。
“谢谢你,林晚。”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。
她眼圈有点红,却摆摆手:“快走吧,别误了火车。”
在外地进修的半年,我常常想起林晚。
想起她蹲在机床边记笔记的样子,想起她递过来的带花香的手帕,想起她系在操作台上的白纱巾。
我给媳妇写过一封信,说我们可能不合适。媳妇回信骂我“翅膀硬了”,让我“滚回来离婚”。
半年后,我回到厂里,成了技师。
第一件事,就是去劳资科找林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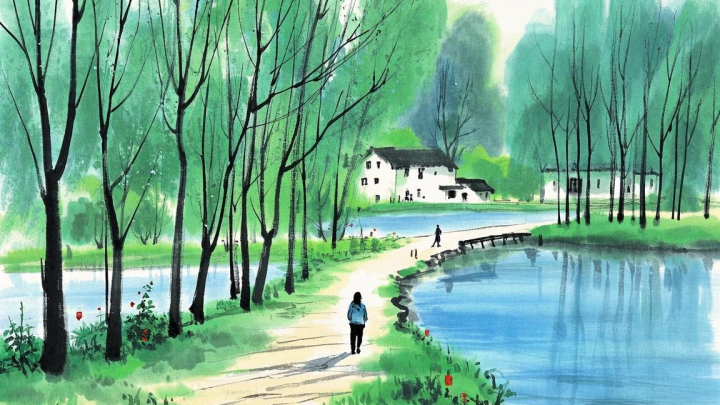
可科室的人说,林晚上个月调走了,去了局里的档案室。
我心里一沉,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。
我去局里找过她,门卫说“非请勿入”。我在局门口等了一下午,也没看见她的影子。
后来,我跟媳妇离了婚。
她卷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,临走前还骂我“活该打光棍”。
我没觉得难过,反而松了口气。
离婚后的日子很简单,上班,下班,偶尔跟老伙计们喝两盅。
我把机床擦得锃亮,把操作台收拾得井井有条,好像这样就能留住点什么。
有一次,厂里开技术交流会,我在局里的会议室看见了林晚。
她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套裙,头发盘起来,戴着细框眼镜,跟当年那个扎麻花辫的姑娘判若两人。
她正在给参会人员发资料,动作麻利,神情干练。
我看着她,心里五味杂陈。
她也看见了我,愣了一下,然后走过来,递给我一份文件。
“陈技师,好久不见。”她的语气很客气,像对待陌生人。
“好久不见,林科长。”我接过文件,手指触到她的指尖,还是有点凉。
“你现在是技术骨干了,”她笑了笑,笑容很公式化,“恭喜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能干巴巴地回应。
交流会结束后,我在局门口又看见了她。
她正在等车,手里拿着个文件夹,白纱巾不见了,换成了一条素色的丝巾。
“林晚,”我鼓起勇气走过去,“当年……谢谢你的饼干。”
她转头看我,眼神平静无波:“陈技师客气了,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
“我……”我想解释,想告诉她这几年我常常想起她,可看着她疏离的样子,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“我的车来了,”她指了指远处驶来的公交车,“再见,陈技师。”
她上了车,车窗关起来,把我和她隔在两个世界。
我站在原地,看着公交车开走,心里空落落的,比离婚那天还要难受。
后来,我听说林晚结婚了,丈夫是局里的干部,长得一表人才。
我心里有点堵,但也替她高兴。她那么好的姑娘,本该有更好的生活。
我继续在车间里干活,从青年熬到了中年,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,头发也开始花白。
有一年冬天,厂里搞退休职工茶话会。
我作为老技师代表参加,在会场里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是林晚。她头发白了不少,也胖了些,穿着件厚实的羽绒服,正扶着一位老太太说话。
老太太我认识,是以前劳资科的老科长,林晚当年的师傅。
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走了过去。
“林……林姐,”我斟酌着称呼,“好久不见。”
她转过头,看见我,先是一愣,然后笑了,眼角的皱纹堆起来,像盛开的菊花。
“哟,是建国啊!”她的语气又变回了当年的爽快,“都老成这样了!”
“你也一样,”我看着她,“头发都白了。”
“可不嘛,”她拍了拍我的胳膊,“都快退休了,能不老吗?”
老科长笑着说:“你们俩啊,当年在车间可没少打交道。”
林晚笑了笑,没接话。
茶话会结束后,我们一起往外走。
外面下着雪,雪花落在头发上,很快就化了。
“建国,”林晚忽然说,“当年你去进修,我给你装的饼干,其实是我自己烤的。”
我愣住了,看着她。
“那时候我刚开始学做点心,”她看着远处的雪景,眼神有些飘忽,“本来想等你回来,再给你做点别的……”
她没说完,我也没追问。
有些话,错过了就是错过了,像落在地上的雪,化了就没了痕迹。
“你现在过得好吗?”我问。
“挺好的,”她点点头,“老伴对我不错,儿子也成家了。你呢?”
“我也挺好的,”我笑了笑,“一个人过,清净。”
“挺好,”她也笑了,“一个人自在。”
走到路口,她要往东边走,我要往西边走。
“那我先走了,建国。”她挥了挥手。
“你也慢点走,林姐。”我也挥了挥手。
她转身走了,雪花落在她的羽绒服上,像撒了一把盐。
我站在原地,看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远,直到消失在风雪里。
忽然想起很多年前,在那个机油味弥漫的车间里,她扎着白纱巾,蹲在机床边对我笑。
那时候的阳光很暖,透过窗户照在她身上,把白纱巾染成了金色。
而我手里的扳手,还留着她指尖的温度。
现在,什么都没了。
只有机床还在嗡嗡地转,像在唱一首关于青春和遗憾的老歌。
我裹紧了棉袄,迎着风雪往家走。
路上的雪很厚,踩上去咯吱作响。
不知道为什么,我忽然很想再吃一次她做的饼干,哪怕已经忘了是什么味道。